马上注册,结交更多好友,享用更多功能,让你轻松玩转社区。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立即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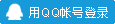
x
《草根传》节选丨第一章:新手
2008年8月,中国第一次在家门口办奥运。北京天空的蓝,浓郁得像深海。
下班后,瓶子沿着宣武门地铁口的台阶,一步一步走上地面,迎入视野的开阔和高远,让她的心像飞翔的小鸟一样舒畅。
新婚不久,丈夫是网络公司的技术员,虽然两人毕业都才三四年,但工作已逐渐稳定下来,工资加起来每月也有七八千。
瓶子在心里归置了一下,是时候买下个小居室,有个孩子了。目前的收入用于房贷的分期付款已够了,只是首期还有些缺口。
娘家指望不上,老家在一个贫瘠的乡村,爸爸妈妈和一个哥哥靠种几亩薄田为生,平时度日尚可,但想做些开销大点的事,都还得找瓶子凑点钱,添把手。婆婆家景况要好些,答应到时会支援他们一些。
一个农村出来的女孩子,能在北京,这个从小就无比向往的城市扎下根,她的步伐和笑容里都流溢出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幸福。
转乘公交车,车上的广播除了报站,还配上了背景音乐,好多明星在一起联唱《北京欢迎你》,她最喜欢其中的李宇春。
北京欢迎你 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魅力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 在阳光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上刷新成绩……
瓶子在心里和着曲,见一位老爷爷刚上车,便直起身来让座,这时手中的电话响了,是哥哥从老家打来的。
凡高在厨房里热饭菜,油烟渐起,顺手打开排风扇,听见客厅门的关合声,知道这个点是瓶子到家了,他转身探出头,想和往常一样打个招呼,却见她闭皱着双眼,斜倚门框,身子正慢慢无力地往下坠。
“瓶子?瓶子?”凡高焦急地呼喊。
瓶子无力地睁开眼晴:"我哥说,妈肚子痛都快一个月了,一直没告诉任何人,每天都自己偷偷去卫生所打吊针,人一下子瘦了好多。昨天他们发现后送她去了县医院,CEA已超过600,医生怀疑是结肠癌。"
"CEA?结肠癌?"凡高看着蹲在地上,泪水盈盈的瓶子,一时懵怔得什么都反应不过来。
过了好一会,凡高伸过结实的臂膀,将瓶子揽到怀里,轻声说:"县医院只是怀疑,咱们尽快把妈接到北京来。"
北京一家肿瘤医院根据增强CT作出的诊断让瓶子彻底崩溃:肺癌,双肺弥漫性转移。副主任医生用迟缓却不迟疑的语气告知,已错过了有效治疗的时期,生存期大约还有两三个月,病人收入医院已没有意义。
"收入医院已没有意义?"
瓶子连想都没有想到过,生命垂危的妈妈会被医院拒收。她一直以为,无论什么时候,无论遇到多大的病痛,医院理所当然该是生命的最后庇护所。
因为术有专攻的医生在这里,只有他们才知道癌症的成因是什么;因为经验丰富的护士也在这里,先进的检测仪器也在这里,战斗只有在这里激烈交锋过,甚至也只有在这里结束,才算得真正意义上的回天无力、覆水难收。
而现在,医院却认为,在这里打响战斗的必要都没有。
怎么办啊?妈妈含辛茹苦地把哥哥和她拉扯大,撑起这个家,现在却眼睁睁看着她一天天在消瘦,一天天在痛苦中受折磨,自己却什么事都做不成,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,迷惘、压抑、无助。
她一定要干点什么,一定要朝着给妈妈治疗的方向去奔走,越疲惫,越劳累,也许越能消磨心中的苦闷和痛触。
一位部队医院的年轻大夫接诊了她,是她,不是她妈妈。妈妈已弱不禁风,这几天,她带着肿瘤医院的影像和诊断报告到不同的医院去求救。
年轻大夫很细致地看了CT片后说:"已扩散,不能手术,如果治疗,我们要穿刺取组织,先做个病理检查,如果你们经济条件允许,也可在穿刺的同时取组织做个基因检测。但原发灶位置比较特殊,病人又已虚弱,必须入院才能进行。"
"能入院?"瓶子眼前一亮。 "现在不行,我先做个预约登记,一旦有床位空出来就会通知你。" "住进医院后,会有哪些治疗?" "不一定,得看检查情况。一般会做四个周期的化疗,之后评估效果。" "你刚才说如果经济条件允许,可做个什么检测,很贵吗?它起什么作用呢?" "基因检测,大约一万元一次,如果化疗没效,基因检测报告能提示你能不能用靶向药易瑞沙。"
瓶子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很有耐心的医生,"易瑞沙多久用一次?每次注射都要重新办入院手续吗?"
由于之前的拒收,她对"入院"已有种本能的条件反射。"易瑞沙是口服药,每天一粒,不用入院。但一个月要一万五,六个月之后如果仍有效,会免费赠药。"
走出医院大门,瓶子深呼了一口气。天还是那么高,那么蓝,而短短的十几天,她的心却已低沉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但刚刚的求诊让她在茫然中又看到了希望,年轻大夫讲的东西,在她脑子里隐隐约约形成了一条治疗的线索。想到爸爸和哥哥现在正像困兽一样躁动、焦虑、沮丧、一筹莫展,她怱怱往回赶。
出乎意料的是哥哥和爸爸的沉默。
一到家,她竹筒倒豆似的把在医院的情形说了个遍,哥哥追问了些细节,之后就没人再吱声。半晌,爸爸擦了擦湿润的眼角,起身去了妈妈卧床的隔壁房间。
第二天一早,哥哥说想跟瓶子一起出去转转。两人穿过熙熙攘攘的菜市场,走到略为僻静的地方,哥哥话说得吞吞吐吐,意思是他们仨已商量好,准备这一两天就回乡下。
瓶子怔怔地站住了。哥哥叹息:"治不起啊。老家得这个病的人也不少,只要知道是这病,也就不治了,拿什么治啊?真的痛了,就去镇上的卫生院,医生怎么说咱就怎么办吧。"
瓶子心里好悲切,她也是从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长大的,她懂得哥哥那句"治不起"背后的酸楚和无奈。即便是把值不了多少钱的祖屋也卖掉,对于日出几千,动辄几万,无底洞似的医院治疗费,也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。
两人默默地往回走,瓶子明白,一旦他们回老家,她也就再也握不到妈妈的手了。她喃喃地对哥哥,也是对自己说:"给我点时间,迟点回乡下,再给我点时间吧?"
给点时间又能干什么?年轻大夫说的话,无形中成了她坍塌内心里的唯一支撑,但那不是所有得了这病的人都在走的路吗?
最后的结果并不难猜测,而且她也支付不起这笔巨额的费用呀,不知道,也想不明白,只有种强烈的愿望,就是想抓住妈妈,不撒手。
夜晚,瓶子两口子的小房间,凡高告诉瓶子,昨天听她从医院回来提到易瑞沙,今天就在网上搜索,发现有个综合网站里的小分类,里面有不少人在谈论这个药。
"真的?"瓶子很惊异,但似乎也太渺茫。
那个一天就服一粒的小丸子,在年轻大夫介绍的治疗链中,排到了入院穿刺、多次化疗无效和基因检测之后,而且是天价。也许到那一天,她早已弹尽粮绝,即便想坚守,日子怎么过,她现在已无力去想象。
但比想象更难熬的是等待。
三天过去了,没有医院的任何消息,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蚊。电话去问,得知排在她前面的人还很多,人病到这种程度,哪能不吃药?
她带着妈妈去挂了一京城名老中医的号,抓了十副药,天天煎汤服。有几天刚喝几口,就连同之前呡进去的粥水一起吐出而出。十天中又去了两次那所部队医院,结果是,登记在前的人仍不少,还得等。
又一天一天往前熬,音讯全无。看着妈妈的脸越来越蜡黄,脚的浮肿已漫过双膝,胸闷,时而气喘,时而呼吸短促。瓶子心急如焚,一天天加重的腹胀腹痛和腹水,成为了压垮她那脆弱支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当爸爸再次跟她说准备动身回老家时,瓶子低下了头,没再坚持,绝望地默认了。
又是夜晚,还是两口子的小房间,仍是结实而熟悉的臂膀,凡高揽着身心俱疲的瓶子,他们依偎地靠着,谁也没有开口说话。
过了很久。凡高问:"还记得前几天我跟你说过的那个网站吗?" "嗯,记得,怎么了?" "有几个人在上面说,吃了易瑞沙之后,体感神奇般的好转。" "医生说第一步是化疗,第二步才是靶向药,我们第一步都做不到。"瓶子黯然地说。 "有个叫‘憨豆精神’的人,他在帖子上说,他用易瑞沙之前没做化疗。" "那他做了基因检测吗?"瓶子向上扬起脸,去看丈夫。 "好像是做了。" "我们什么都没做,而且进不了医院,没有医生开的处方,我们也买不到易瑞沙。" "有网友说,他们是托亲戚朋友到去买的,那里不受限制,还便宜很多。" "啊?"瓶子的嘴惊讶成了O型,"便宜到什么程度?"她直起身子,侧过来对着凡高。 "据说一个月也要好几千。" “好几千?每个月好几千,再加上每个月的房租,也就是说,用尽他们这个小家每个月的全部收入,也许能刚刚凑上这个数?” 凡高似乎读得懂瓶子眼中闪过的空洞,低声说:"我们试一下?我知道,不试你会遗憾一辈子的。"
她没想到,平时话不多的丈夫会在她已万念俱灰的时候,擦亮一根火柴,点起一根蜡烛。苦痛干裂已久的心,如逢甘露。自得知妈妈患病以后,这是第一次,瓶子的嘴角有了一丝向上的弧度,她对凡高说:"那我们以后,还会吃得起方便面吗?"
丈夫略带笑意,低头对她说:“确实,为给妈妈治病,我们就暂时不能考虑要孩子,也暂时不能考虑买房子了。”
运气终于站到了瓶子一边!易瑞沙有效。瓶子狂喜!
她当然指望易瑞沙有效,甚至每天去上班之前,都会坐在卧室的梳妆台前默默地为此祈祷一会儿,但真的看着妈妈就凭这一天一颗的小小药丸,状态在快速地好转,她除了兴奋,就是惊讶。
最近只要手头上的事一空下来,她都会去看凡高介绍的那个网站,那个小分类里,聚集的全是同类人,不是本身患有肺癌,就是患者的家属,聊的都是治疗上的事。
她几乎什么都不懂,能说的话也不多,但她很愿意沉浸在其中听他们倾诉,有些她感同身受,有些正好能解答她心中的困惑。
她发现,其他人的治疗都是从手术或化疗开始的,像她这样茫然中首先就闯向易瑞沙的人好像还没有。
另外,她最喜欢看"憨豆精神"的帖子,在群里大家都称他"憨叔"。憨叔本人是患者,在他的帖子里,她第一次知道了易瑞沙会耐药,也就是用过一段之后药就会失效。
憨叔用的药也是易瑞沙,他正在绞尽脑汁、左尝右试地想从这耐药中杀出一条生路,尽管其中的一些做法她连想都不敢想,但憨叔会在他的一段段帖文中,将试药前的所思所想,以及尝试后的检测和评估都娓娓道来。
用词遣句中的那种从容不迫,生死转折之间偶尔淡淡丢出的一两句调侃和幽默,无形中透射出的力量,会让她焦虑浮躁的心在不知不觉中平复很多。
北京已是严冬,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滑过一样生痛,但如直接站立在太阳的光芒之下,并不觉得冷,甚至还有些辐照下的烘暖。
服易瑞沙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,瓶子扶挽着妈妈,在清华校园里环绕着荷塘慢慢散步。池水的表面已冻成了一尺来厚的冰层,三五结伴的人群,穿着溜冰鞋,在上面尽兴地来回穿梭。有个初学的男孩,跄踉了几步,一个四脚朝天,摔出一丈多远,爬起来时,龇牙咧嘴地做了个搞怪的样子,引得瓶子的妈妈大笑不止。
瓶子已很久没见过妈妈发自内心的欢笑了。当妈妈的病随着哥哥的一个电话像海啸般铺天盖地向她席卷而来时,她觉得自己无力无助得比一只蚂蚁还渺小。
她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狰狞恐怖的魔鬼,神圣的医院都望而却步的不治之症,在一颗小小的易瑞沙面前,会像大海退潮一样悄然无息地畏缩,难道它是上帝派来了天使?
她不可能知道,更没特殊的感知,但冥冥之中让她妈妈起死回生,让易瑞沙进入她视野的,确有其人。
第一章完
|